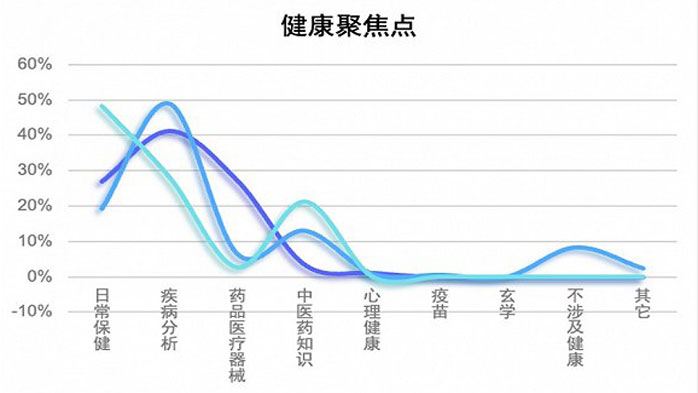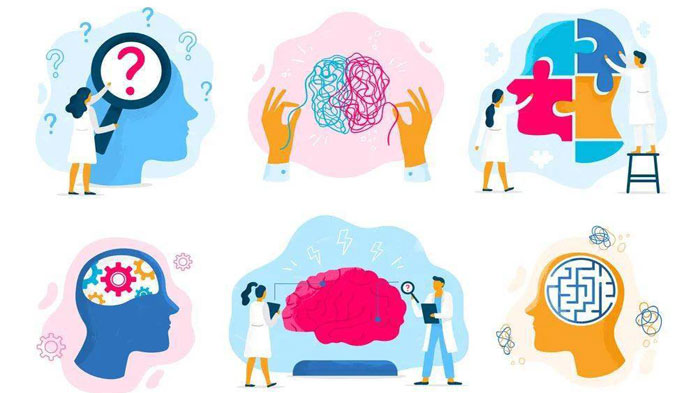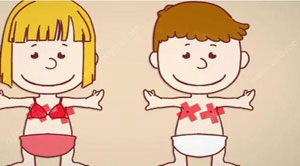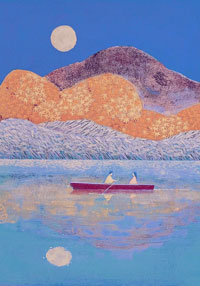李勇生:在看不见的世界里,用心理咨询救人救己
发布时间:2023-12-04 09:39:05 | 来源:中国网心理中国 | 作者:慕宏举铃声响起,李勇生迅速戴好耳麦,接通电话。他可能会听到“我不想活了”的大吼,也或许是压抑不住的痛哭,还可能是自言自语的低喃,抑或是令人不安的大段沉默。
捕捉声音和其中的情绪,本就是李勇生最擅长的事,作为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,他要做的就是快速分析来电者的心理状态,然后有针对性地沟通、劝导,有时充当倾听者,有时化身劝慰者,一直守在“死门”前。
一个电话可能要打很久,时间的流逝李勇生只能通过感官来判断——打在身上的风变凉了,那就是太阳落山了,街上人声车声渐多,上下班高峰到了。李勇生今年41岁,失明31年。
年幼失明,他跌跌撞撞闯世界,急切地证明自己即便看不见,也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,自卑又骄傲。做盲人心理咨询师,他试图走进别人的内心,治愈他人的同时,与自己和解,在助人与救己中,寻找人生的意义。

李勇生。受访者供图
眼睛以上,全是“雷达”
十月的一个下午,天津郊区的一个小院里,李勇生坐在院里等着来访者。人走到他面前两米时,李勇生抬起头,向着脚步传来的方向站起身,伸出右手,过程干脆利落。
“你好,欢迎,走,我们进屋里聊。”
手被抓住握两下,李勇生“看”向来访者,他墨镜后的双眼,右眼紧闭,左眼微张露出灰蓝色的瞳孔,无神。
盲人的姿态更多显现出来。他右手向前试探地摸索,走到门边,头微微低下——尽管站直后他的头顶距离门框还有很大距离;在熟悉的走廊里,他的步子迈得很大,但身体忽左忽右,直到摸到右侧墙壁上的扶手,该右转了;进屋后,几步之外就是桌椅,当脚尖踢到桌腿时,他停了下来,沿着桌子边缘摸到了紧挨着的木椅,转身,双手向后握住椅把,缓缓坐下。
心理咨询正式开始。
倾听时的李勇生头略低着,眼睛“看”着对方,时不时挑下眉毛,耳朵不经意地抖动,像是打开了全部的感知“雷达”。他很快捕捉到了对方细小的动作——对面那个声调高亢的年轻人,一会儿跷着二郎腿,一会儿又双手摸着膝盖,时而坐直了身体,时而靠在椅背上。
李勇生心里有了判断,这是个内向、心思细腻、不太成熟的大男孩。“可能也就1秒”,李勇生这样描述他的感知速度,他用自己的经验解释,“音调高的人往往心思细腻,那些声音低沉、坐着不乱动的人一般城府较深,他绝对不是,甚至不够成熟。”
谈话不知不觉间进行了三个小时,李勇生问来访者:“天黑了,要不倒点水再继续?”
他面向窗口接着说,“窗外的鸟已经从叽叽喳喳的啼叫变成一声一声的低鸣,凉气也灌进我衣服里了,最近天津温差大,有点儿凉,我也是想穿件外套。”
似乎感知到了对方的诧异,李勇生指了指自己的眉心,又以眉心为起点,沿着眉毛、耳廓上方、后脑勺画了一个圈,“这个圈以上都是我的感知区域,像雷达一样。”

李勇生做心理咨询时喜欢与来访者一起坐在沙发上。受访者供图
失明是件心酸且自卑的事
李勇生并非天生失明,坠入黑暗前,他眼前的最后一个画面是,被鲜血染红的雪。
那是一个初冬的中午,在山东德州老家的村子里,10岁的李勇生和小伙伴打闹时,一跤摔在了路中间的铁磅秤上。
爬起来后,他摸了摸自己的眼睛,原本应鼓起的右眼瘪了。依靠左眼依稀的光亮,他看到滴落的血染红了周围的雪。
当晚,李勇生做了眼球缝合手术,醒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,只觉得头顶很重,“像箍了顶铁帽子”。他摸着脸,双眼被一层层纱布裹住,世界一片黑暗。也是从那时起,他总会下意识摸头顶,“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,想把它摘下去,总觉得头顶戴了铁帽子,持续了很多年。”
突遭剧变的李勇生还没来得及理解失去双眼意味着什么,只知道一切都变了。“早晨”由射进家里的第一束光变成了麻雀的第一声啼叫。身体对温度变化的感知更精细了。当“温暖“与叽叽喳喳的麻雀声同时出现时,屋外便是晴朗的好天;而潮气和扇动翅膀的声音同时出现,他断定,一场大雨即将来袭。
直到那些背后议论的声音四起,他才意识到,失明竟是件心酸且自卑的事情。
不舒服的感觉并非猛烈的,难过的瞬间总是悄无声息地出现。“多好的孩子啊,这辈子算是废了。”亲戚无心的一句话,直直扎进李勇生的心里。
酸楚渐渐堆积,自卑从中发酵。原本活泼开朗的孩子成了走路都踉跄的盲童,他参与不进小伙伴们的游戏和话题,不能再上树掏鸟、下河摸鱼,春天的绿草、夏天的蓝河、秋天的黄叶和冬天的白雪,在他的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和意义。
失明后,李勇生的脑海里总会涌现出“昙花一现”的理想。听着电视剧里军人铿锵有力的口号声,想着自己要是能看见,或许能去当兵;听着新闻里播报航天员搭乘飞船上了太空,他也想知道太空是什么样子。
理想穿插进残酷的现实,总会带来短暂的失落,而这一切都和失明有关。“虽然没有直接的伤害,但总有不舒服的地方,就像胸口压了块石头。”
跌跌撞撞闯世界
或许是骨子里天生要强,也或许是想摆脱自卑,李勇生总想证明自己与常人无异,“别人越说我做不了,我越想做出来给他们看。”
当具象化的物品变得模糊,勇气就占据了上风。以往怕蛇又怕鬼的李勇生,不仅敢徒手抓蛇,也敢一个人闯进漆黑的小路,还敢爬上三层楼高的树杈。
他一点点摸熟了村里的路,一块不起眼的石头,墙壁凹进去或凸出来的石砖,地面的斜坡都是指路标识,“地图”在脑子里渐渐成形,他扶着墙壁就敢大步快速向前。
村西头几米深的河,常有村民掉东西进去,村民嫌脏、怕深,只有李勇生愿意脱下衣服憋足一口气扎进去,在淤泥中摸索失物,每找到一件,可以得到几毛钱的“辛苦费”。上岸后,他来不及冲洗,带着一身河腥味将钱换成冰棍,一路嗦着回家。一来二去,李勇生的水性越来越好,找他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,他第一次觉得“挺自豪”。
后来,为了改善家里生活,李勇生父母带着他和弟弟去天津打工,一家四口住在了郊区的村子里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最远只走到家门前的胡同口,再往外走,母亲便以看不见为由命令他不许胡来。
离开了熟悉的环境,一切都要从头再来。凭借一根竹竿,一双沿着墙壁摸索的手,李勇生将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胡同扩大到村里,又从村里走向村外。
有限的地图慢慢展开后,他的野心越来越大。找来朋友提前写好“我没事儿,一切平安”的纸条留在家里,李勇生偷偷带着自己攒下来的零花钱和一根竹竿,独自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哈尔滨,一路边走边问。
带的盘缠即将花完,他低价从小贩手里买来一大包笛子,再高价倒手卖出。闻到饭香时,他听听排风扇的声音,“声音大的是大饭店,不去,声音小的可以进去饱餐一顿。”
流浪一段日子,再安然无恙地回家,李勇生证明了自己“能行”,从那之后,家人再也没有限制过他的自由。
与自己和解
声音,在李勇生看不见的世界里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。
在老家的那些年,每当暖风吹到身上时,他便一个人走出家门,凭借脑海中的地图去“有声音的地方”。
当听到“哗哗”的声音,感受到周围的温度也降了几分时,他便知道此行的终点到了——河边一棵茂密的大树。他拍拍脚下的泥土,找到最柔软的地方,一屁股坐下去就是几个小时,头顶不时传来“沙沙”的声音,他知道,绿叶正在风中舞动。
不出门的日子,最好的伙伴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。打开开关,相声、评书、二人转一股脑地闯进他的世界。
深夜收音机里心理咨询节目最多。一次拨打电台热线时,李勇生连线上了心理咨询专家,谈及未来,专家说,不如做一名心理咨询师。
从那之后,“心理咨询”这几个字在李勇生心里扎了根。但真正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却没那么容易,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很多年。

李勇生的心理咨询室开在按摩店旁边,他说现在偶尔也接一些按摩的工作,但比以前少多了。受访者供图
李勇生一直记得刚开心理咨询室的时候,自己的忐忑和无措,“既希望有人来,又害怕有人来。”
在前期通过QQ或电话与咨询者沟通时,他不敢袒露盲人的身份。线下见面时,总会有人因为咨询师是个无法看到自己表情、连个眼神都不能回应的盲人,而选择离开。
进入心理咨询阶段也不顺利,遇到难以理解的人,李勇生经常表现得不耐烦。他记得,一个已婚男人向他倾诉“从小到大被父母宠惯了没受过半点儿委屈,爱花钱却被媳妇限制”,李勇生想到自己的经历,越听越觉得“不可思议”,坐也坐不住,一会儿跷二郎腿,一会儿摸摸头,反复拿起手机听时间,简直度秒如年,连对方都能感觉到他“听不下去了”。
听不下去,也是专业性不够的表现,李勇生知道自己的问题。一个半路出家的盲人心理咨询师,很多时候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
和绝大多数盲人一样,李勇生的学业、工作没有太多选择。上盲校,学按摩,毕业开个按摩店维持生计,日子一眼看得到头。“心理咨询”的种子只能在角落里野蛮生长。
学校没有心理学课程,他就去图书馆找几本盲文版心理学理论书籍,自学得一知半解。用开按摩店赚的钱买了电脑,下载大量心理学课程视频,搜罗全国各地关于心理咨询讲座的信息。遇到讲座费用不贵的,便背着包,拿着盲杖,千里迢迢地赶过去。
2008年,李勇生报名了中残联面向残疾人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。现在回忆,李勇生觉得那是段充实且疯狂的日子。每天除了做按摩就是学习,天蒙蒙亮就起床,一遍遍听视频,直听到能背诵下来,晚上再复习巩固。
两年后,李勇生顺利通过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,2013年又考下了二级。
一次次心理咨询,对李勇生来说,也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。他不再忌讳告诉咨询者,自己是个盲人,听到别人的非议与嘲讽时,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气不过怼回去,甚至他可以笑着调侃自己失明后遇到的糗事。
女儿问他为什么眼睛看不见,他逗女儿,“看手机看的。”年过四十,李勇生早就接受了自己是个盲人的事实,只是偶尔,他还是遗憾。
李勇生记得,一次他和妻子夜爬泰山,日出时,身边的人都在为跃出地平线的朝阳欢呼,只有他看不见,喜悦转化为心酸,寒冷又多了几分。
“我不恨命运的不公,但如果可以,我依然希望能再次看到这个世界。”

李勇生与家人外出旅游时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“助人救己,就是意义”
从心理咨询,到自杀干预,李勇生的阵地多了一条电话线。
“希望24热线”是一条专门面向企图自杀、有抑郁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热线,全年24小时无休。电话是“400-1619995”,谐音为“要留、要救、救救我”。2015年,“希望24热线”在天津开通专线后,李勇生立刻报名成为了首批志愿者。
他还记得自己加入“希望24热线”的第一通电话,来自一位老人,电话接起的瞬间李勇生就听到了声嘶力竭的五个字:“我不想活了。”
第一次面对“生死”,李勇生随着对方的嘶吼而心跳加速,脑海里快速闪过几句安慰的话,随后又被“万一说错怎么办”挤占。他引导着老人慢慢讲述,自己的语速因为紧张变得比往常快了些。
这是一位被电视购物上的假药贩子骗了半生积蓄的独居老人。“他既然会买药,就说明还想活下去”,李勇生冷静了下来,抓住这个突破点问老人,“世上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没有了吗?”
“也不是,有一个比我大的表哥,每天给我送菜送肉。”
“你看,这就是一个对你好的人,还有谁这么做过?”
“还有……”随着老人一一列举,李勇生顺着对方的话安慰,不到20分钟,老人的气消了,和李勇生平和地聊天,一场生死危机就此化解。
每一通电话背后,可能都是一条摇摇欲坠的生命。李勇生总是很谨慎,生怕哪句话说错了,给对方带来伤害,甚至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。刚开始接线的时候,他紧张得手心冒汗,现在,不到1分钟他就能判断来电者的危险等级,并在脑海里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案。
一个晚上,电话响起,来电者是一名货车司机。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,妻子抛弃了他,留下一个8岁的孩子,天天夜不归宿,泡网吧、抽烟、喝酒,眼看着就要走入歧途,男子喊着“我到底该怎么办”,随后再也抑制不住情绪,放声大哭。
“这是一道过不去的坎,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。”李勇生任凭对方发泄情绪,接线室里安静得可怕,只有李勇生的呼吸声和听筒里传出的哭声。
接线结束,李勇生深吸一口气,打开窗,风吹了进来,街上车流的声音和人们的嬉笑打闹声闯进来,把他重新拉回现实世界。
不是所有人都能扛住不断传来的负能量,天津“希望24热线”开通8年,接线员走了一批又一批,从最初的几百人到如今只剩不到50人。

“希望24热线”接线室,屋子里的每个设施都是志愿者们捐赠的。新京报记者慕宏举摄
李勇生也难免有因为过度共情陷入负面情绪的时候,他的发泄方式是,独自到KTV里吼两首歌,或者带一瓶纯粮烧酒,和朋友在地摊撸串吹牛,第二天起来,又是那个冷静又能共情他人的心理咨询师。
有一种情况他最害怕,就是接通电话后对面平静而空洞的声音,或者是长时间的沉默。
一个冬夜,李勇生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,女孩平静地告诉他,自己正坐在桥上,准备跳下去,然后电话里只剩下“呼呼”的风声。“给我一个了解你的机会”,李勇生不停地说话,试图引导女孩说出自己的经历,慢慢地,女孩有所松动,李勇生趁热打铁,“你找个没风安静的地方,咱们好好聊。”
半小时后,听到女孩走下大桥来到公交站,李勇生狠狠松了一口气,又一个小时,女孩终于放声大哭,李勇生知道,他又拉回了一个人。
8年间,李勇生累计救助上千人,听到过号啕大哭,也听到过嘶声大吼,甚至要承受愤怒谩骂,但他听到最多的还是“感谢”,感谢他的倾听,感谢他的挽救。
这是李勇生最骄傲的时刻,“每个人来到世界上,并不是简单地吃饭睡觉,最起码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,做一名心理咨询师,既能助人,又能救己,就是意义。”(新京报 记者慕宏举)
守护好家庭“微生态” 孩子出现这些情况 家长需警惕2023-12-04
关注中小学心理教师成长:工作被边缘 待遇难保障2023-12-04
心理百科 | 当一个人反驳时,是在反驳什么?2023-12-04
坏情绪让心脏“变形”!被情绪影响的器官,都变成了这样……2023-12-01
心理疗愈小锦囊|这个感恩节,你感谢了谁?2023-12-01
专访彭凯平:如何让孩子活出更美好的生活?心理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2023-12-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