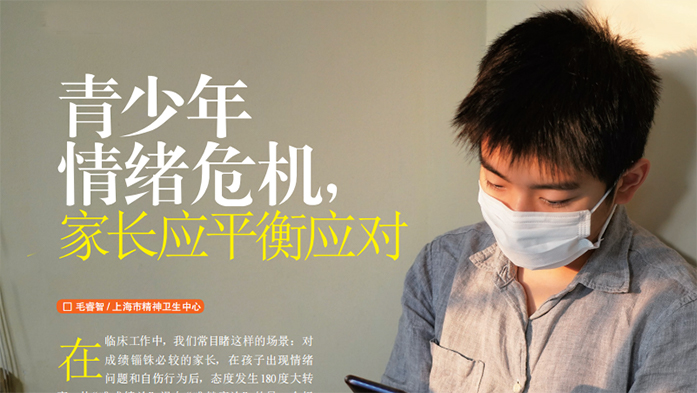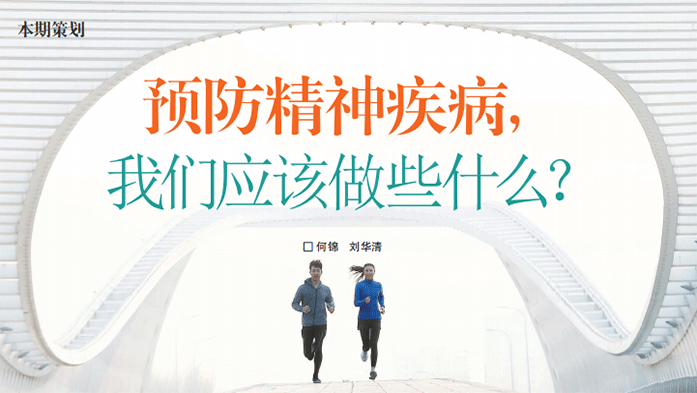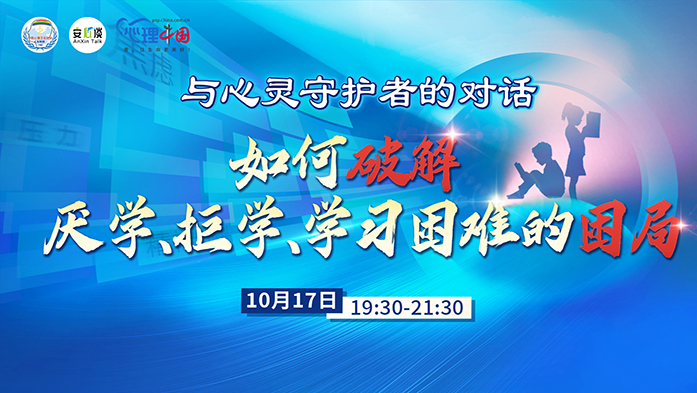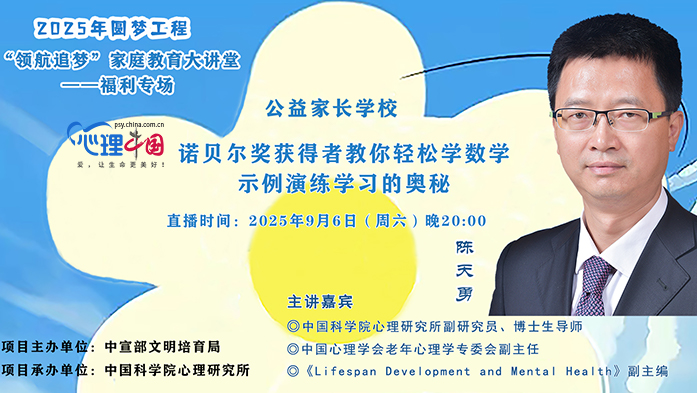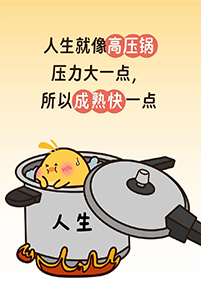心理咨询室 | 迷茫的高二 —— 来自重组家庭高中生的心理辅导个案
发布时间:2025-11-11 15:11:35 | 来源:中国网心理中国 | 作者:吴星中国网心理中国专稿 高二女生小楠,最近像是被一层灰色的雾裹住了。上周的美术社团活动,她没像往常一样带着画板准时出现——要知道,从前她可是社团里最积极的成员,去年还拿过绘画比赛三等奖。课堂上,她总低着头,数学老师提问时,她明明眼神动了动,却还是没举手;课间休息时,朋友们围过来聊周末的电影,她也只是靠在座位上,要么点头附和两句,要么干脆说“有点累,想歇会儿”。
我留意她很久了。小楠高一时成绩稳定在年级前50名,性格虽不算外向,但待人温和,和同桌小林、后桌小宇关系一直很好。可从高二上学期开始,她的月考排名一路掉到了180名。班主任找她谈过两次,每次她都低着头说“我会努力”,可下次成绩还是没起色。更明显的是她的情绪,有次晚自习前,我路过教室,看到她对着作业本偷偷抹眼泪,听见小林问“怎么了?”她赶紧擦了擦眼睛说:“没事,风迷了眼”。
直到上完《亲子沟通的艺术》这堂心理课。下课铃响后,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,小楠却磨磨蹭蹭地留在最后,双手攥着课本边角,指尖都泛白了。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又快速低下头,声音带着点哽咽:“吴老师,这节课……我听着特别难受,能和您聊聊吗?”
问题溯源:重组家庭里的“夹心人”
走进心理辅导室,小楠坐在沙发上,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开口。她的声音很轻,却每一句都透着委屈:“老师,您讲亲子沟通的时候,说‘家人会看见你的辛苦’,可我觉得……没人看见我。”
小楠的父母在她初三那年离婚了。“那时候我正准备中考,他们每天关着门吵架,我在房间里刷题,耳朵里全是摔东西的声音。”她说着,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套,“后来爸爸说‘过不下去了’。妈妈收拾东西走的时候,只抱了抱我说‘好好读书’,然后就去南方再婚了,现在一年也就打两三次电话。”
父母离婚后,小楠跟着爸爸生活。高一下学期,爸爸告诉她要再婚——对方是爸爸的同事,带着一个刚上初一的弟弟。
“第一次见阿姨的时候,她给我买了我喜欢的草莓蛋糕,还说‘听说你喜欢画画,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去看画展’,我那时候还觉得……maybe家里能有点温暖。”小楠的嘴角牵了牵,像是在回忆那段短暂的轻松时光。
可真正住到一起后,一切都变了。继母对弟弟格外上心:每天早上给弟弟准备专属的爱心早餐,晚上陪弟弟写作业到10点;但对小楠,更多的是“要求”——“你是姐姐,要给弟弟做榜样”“高二了,别总想着画画,多刷两道数学题”“这次月考怎么又退步了?是不是心思没在学习上?”
最让小楠难过的是上个月的事。她攒了很久的零花钱,买了一本绘画教程。弟弟看到后,非要拿去画画,她没同意,两人争执起来,弟弟不小心把书撕坏了一页。继母听到声音跑过来,没等小楠解释,就先对着她喊:“不就是一本书吗?你让着弟弟怎么了?他还小,你都高二了,怎么这么不懂事!”
“我那时候特别委屈,就去找爸爸说。”小楠的声音低了下去,“可爸爸说‘你阿姨也不容易,弟弟刚到新环境,你多担待点’,还说‘我最近忙项目,你别总惹家里不开心’。”
从那以后,小楠再也没跟爸爸提过家里的事——她知道,爸爸夹在中间左右为难,可她心里的委屈,却连个能说的人都没有。
“现在我回家就躲进房间,要么写作业,要么躺着发呆。阿姨不怎么跟我说话,弟弟也不跟我玩,爸爸总加班,家里静得可怕。”小楠吸了吸鼻子,“有时候我会想,是不是我不够好?所以妈妈走了,阿姨也不喜欢我,连成绩都越来越差……”
家庭变故对小楠的深层影响
听完小楠的诉说,我心里沉甸甸的。对高中生来说,他们正处于“自我同一性”形成的关键期,既需要家庭的稳定支持,也需要通过学业、兴趣确认自己的价值。而小楠经历的家庭重组,恰好打破了她对“家”的安全感,也动摇了她对自我的认知。
从情绪层面看,小楠的委屈、焦虑和自我否定,源于“安全感的两次崩塌”:第一次是父母离婚,她失去了完整的家庭;第二次是重组家庭的矛盾,她以为能得到的温暖没了,反而成了“多余的人”。这种反复的失落,让她陷入了“我不值得被爱”的负面认知,所以才会在情绪低落时偷偷哭泣,甚至回避和朋友交流——她怕自己的“糟糕”会被别人嫌弃。
从学业层面看,小楠的成绩下滑不是“不努力”,而是“没力气努力”。心理学里有个“心理能量守恒”的说法:当一个人把大部分能量都用来应对负面情绪时,留给学习的能量自然会减少。小楠既要承受继母的高期望和比较,又要消化自己的委屈,还要担心“成绩差会更不被喜欢”,这种多重压力让她在学习时无法集中注意力,甚至对曾经擅长的数学产生了抵触心理。
从社交层面看,小楠的回避不是“不想交朋友”,而是“不敢暴露脆弱”。她知道朋友们关心她,可她怕自己的家庭情况会被笑话,更怕朋友们知道她“过得不好”后,会慢慢疏远她。这种对“被抛弃”的恐惧,让她主动关闭了社交的大门——就像她放弃美术社团一样,因为在社团里,她需要和人交流、展示自己,而现在的她,连“面对自己”都觉得吃力。
从自我认知层面看,小楠把“家庭矛盾”和“自我价值”绑在了一起。继母的指责、爸爸的忽视、妈妈的疏远,在她眼里都变成了“我不够好”的证据;成绩下滑更是加重了这种认知,让她陷入了“我不行”的恶性循环。这种低自尊的状态,会让她越来越不敢尝试,甚至刻意回避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事——比如画画,因为她怕“连喜欢的事都做不好”,会彻底否定自己。
心理辅导策略:帮她找回“属于自己的光”
小楠在辅导室里哭了很久,说完这些话后,她长长舒了一口气:“老师,其实这些话我憋了快半年了,说出来好像……没那么难受了。”但我知道,一次倾诉只能暂时缓解情绪,要帮她真正走出困境,还需要具体的方法和持续的支持。
(一)情绪ABC日记:学会“拆解”负面情绪
我问小楠:“如果下次再遇到阿姨指责你,或者成绩没考好,你除了难过,还能做什么?”她愣了愣,摇了摇头。
于是我给她介绍了“情绪ABC理论”:A是发生的事件,B是你对事件的想法,C是你的情绪和行为结果——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让你难过,而是你对事件的想法让你难过。
我给她准备了一个带插画的笔记本,让她试着写“情绪ABC日记”:
记录A(事件):比如“继母拿我和弟弟比,说我不够懂事”;
分析B(想法):“她就是不喜欢我,觉得我是累赘”;
反思C(结果):“难过、不想说话,晚上没心思写作业”;
换个B(新想法):“她可能更担心弟弟的适应,不是针对我;而且‘不懂事’只是她的看法,不是真的我”;
新的C(结果):“没那么难过了,先把作业写完,明天再跟她好好说”。
“写日记的时候,不用怕写得不好,也不用强迫自己‘必须积极’。”我拍了拍她的肩膀,“哪怕只是把‘我今天很难过’写下来,也是在和自己对话。如果遇到解不开的情绪,就带着日记本来找我。”
(二)家庭沟通指导:用“我信息”代替“指责”
小楠最在意的,其实是“爸爸能不能看见她的委屈”。
我问她:“如果下次爸爸再跟你说‘你多担待点’,你想怎么回应?”她想了想说:“我想告诉他‘我也很难过’,可我说不出口,怕他觉得我不懂事。”
于是我教她用“我信息”沟通("我信息"是由心理学家托马斯·戈登提出的非指责性沟通方式,避免在亲子沟通中激发对抗情绪)——不指责对方,只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比如把“你从来都不关心我”换成“爸爸,当你让我‘多担待’的时候,我会觉得我的委屈没人看见,有点难过;我希望你能听听我怎么说,而不是让我一直让着弟弟”。
“这样说的时候,爸爸不会觉得你在‘挑事’,反而会知道你需要什么。”我给她举了个例子,“比如上次弟弟撕坏你的书,你可以跟继母说‘妈妈,弟弟撕坏我的书时,我很着急,因为那是我攒钱买的;我不是不想让着他,只是希望你能先听我解释’。”
同时,我也通过班主任联系了小楠的爸爸。电话里,我没有指责他,而是客观地告诉他:“小楠最近压力很大,她不是‘不懂事’,而是太想被家里接纳了。您可以试着每周抽半小时,跟她聊聊学习之外的事,比如她喜欢的画画,让她知道您在乎她的感受。”小楠爸爸沉默了很久,说“我以前确实忽略她了,以后会多注意”。
(三)自我价值重建:从“擅长的事”找回自信
小楠曾经最擅长画画,可现在却不敢碰画板——因为她觉得“成绩差,画画也没用”。我从抽屉里拿出她去年参加比赛的作品照片(之前跟美术老师借的),递给她说:“你看,这张画里的光影多细腻,当时评委说‘能感受到画者的温柔’,这是你独有的能力,不会因为成绩或家庭变了就消失。”
她看着照片,眼睛慢慢亮了起来。我建议她:“这周社团活动,试着去看看?不用强迫自己画画,哪怕只是跟朋友们聊聊天,看看别人的作品也好。”同时,我和美术老师尹老师沟通,让老师在社团里提一句“最近想办个小型画展,很期待小楠的作品”——用这种温和的方式,给她一点“被期待”的力量。
另外,我还让她做“优势清单”:每天写下一件自己做得好的事,哪怕是“今天按时完成了数学作业”“给小林带了她喜欢的橡皮”。“这些小事不是‘微不足道’,而是在提醒你:你一直都在做好事,一直都有值得被肯定的地方。”
(四)同伴支持激活:让她知道“不是一个人”
小楠怕朋友笑话她的家庭情况,其实是高估了“别人的关注”。我跟她说:“你觉得小林会因为你的家庭情况疏远你吗?”她想了想说:“不会,她以前总帮我。”“那为什么不试试跟她说说呢?”我鼓励她,“朋友之间的关心,不是‘能帮你解决问题’,而是‘愿意听你说话’。哪怕她只能说‘我陪着你’,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支持。”
后来,小楠真的跟小林聊了自己的情况。据小林说,小楠说完后,还问“你会不会觉得我家很麻烦”,小林抱着她说“我心疼你还来不及,怎么会觉得麻烦”。从那以后,小林每天都会约小楠一起吃饭,周末还会跟她一起去图书馆学习——同伴的陪伴,让小楠慢慢打开了心扉。
辅导成效与反思
两周后,小楠带着日记本来找我。翻开本子,我看到她写的内容:
“10月 15日:今天爸爸问我‘画画最近有没有新想法’,我跟他聊了很久,他还说‘下次带你去看画展’,有点开心。”
“10月 18日:美术社团活动,我画了一幅小画,老师说‘很有进步’,小林还拍了照发朋友圈,说‘我的朋友超厉害’。”
“10月 20日:这次周测数学进步了 10分,虽然还是不算好,但我觉得有希望了。”
她笑着说:“老师,现在回家的时候,我会主动跟阿姨说‘今天弟弟在学校乖不乖’,她虽然话不多,但会跟我聊两句。爸爸也会抽时间陪我写作业了。”看着她眼里的光,我知道,她正在慢慢走出灰色的雾,找回属于自己的方向。
这次辅导也让我明白:高中生的心理问题,往往不是“单一原因”造成的,家庭、学业、自我认知都会相互影响。作为心理老师,我们不仅要帮学生“缓解情绪”,更要教他们“解决问题的方法”——比如如何沟通、如何重建自信;同时,也要联动家庭和学校,形成支持系统,让学生知道“他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”。
小楠的故事还在继续,后续我会继续跟进她的情况,比如每月和她聊一次,和她爸爸保持沟通。我相信,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支持,她一定能在高二这一年,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,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(作者:吴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心理健康教师 中国网心理中国专稿 网址:http://psy.china.com.cn/)
心理问答 | 孩子处于“空心”状态应该怎么应对?2025-11-24
2025年基层精神科护理安全与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将在百色市召开2025-11-24
心理咨询室|打破情感隔离,帮助孩子走出学习困境2025-11-18
每个过分要求的背后,都有不曾被看见的焦虑2025-11-17
“情绪消费”渐起,年轻人更愿意为快乐消费2025-11-14
外媒关注中国推动改善学生心理健康:减轻学业压力、保证体育锻炼2025-11-14